最新科研成果 | 人类活动对我国西南部亚洲象孤立小种群的影响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的亚洲象种群仍属于一支活动范围可延伸至缅甸北部的较大亚洲象种群,目前南滚河象群被孤立在保护区西部的沧源片区,在遗传结构上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分布的亚洲象种群,属于β分支,与国内属α分支的其他种群和缅甸种群存在地理隔离。
南滚河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前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大面积的森林和荒地被用作农田,加之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使得南滚河亚洲象的生存空间在过去30年中被不断地压缩,极易受到活动范围、食物与配偶难以获得等因素的影响,有灭绝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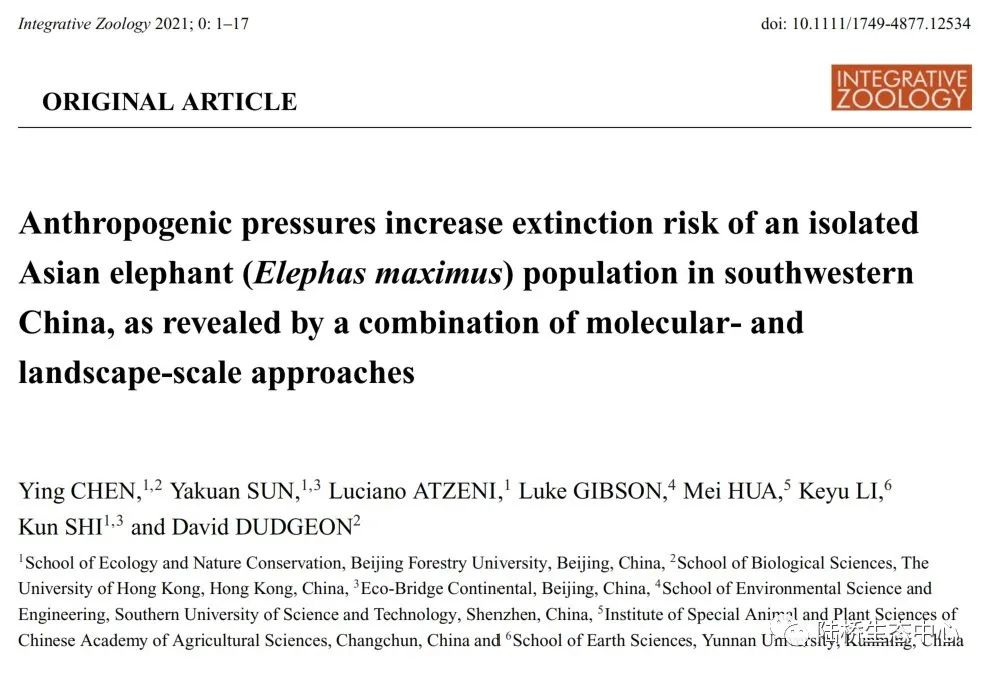
作者团队:陈颖、孙亚宽、Luciano Atzeni 等
-
1989年-2019年30年间南滚河地区的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变化和人口增长)对南滚河象群的分布和生存能力产生了什么影响?
-
适宜栖息地面积的缩减是否会制约南滚河象群的种群发展?
-
外部个体迁移至此区域是否会受到阻碍?由此,南滚河象群的种群数量在未来是否有继续增长的可能?
2018年3月至5月,研究团队在南滚河保护区西部70km²的范围内采集了117份亚洲象粪便样本,提取并分析粪便DNA来判断亚洲象个体的基因型差别、性别和种群遗传多样性指标,并通过测量粪便的周长来判断亚洲象个体大致所属的年龄层。

同时,运用卫星遥感数据对1989年至2019年间南滚河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和亚洲象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动态进行了分析,继而探究这种变化在过去30年中对南滚河象群所产生的影响。

对117份粪便样品中提取的粪便DNA进行分析,共识别出22个独立基因型,其中有13头雄性,9头雌性。从粪便周长判断,象群中有12头成年亚洲象和9头亚成体,仅有1头幼象。
这22头亚洲象个体中的20头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分属于4个家庭单位中的父母-子女或同胞/半同胞兄弟姐妹。

南滚河象群的基因网络。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个体,连结线代表两个节点之间的关联性。节点越大代表其与其他节点(个体)的关联越多;连结线的粗细和个体间亲缘关系的远近成正比。可能存在的不同的家庭单位以不同颜色标识。
分子研究结果显示,南滚河象群的遗传多样性较低,同时近交指数较高,种群生存力整体偏低,近亲繁殖的个体占种群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南滚河种群中幼象比例偏低就可能是因近交衰退导致新生个体的生存率降低,同时,小范围内的高种群密度也会导致生育率下降。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数据模拟预测南滚河象群极有可能在60年内灭绝。
根据亚洲象粪便分布的位点判断,南滚河象群在2018年3月至5月之间仅分布在保护区西部约50km²的范围内。在同一段时间内,南滚河象群的核心分布范围内记录到了打猎、放牧、垂钓、露营等人类活动。

2018年研究区域内(a)亚洲象活动记录与(b)人类活动记录的核密度分布图。
调查区域内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混交林和灌木,共占调查区域总面积的71%;其次为农田和橡胶林,约占调查区域总面积的20%。在1989年至2019年的30年间,农田面积占比下降了1%,橡胶林面积增加了2.7%,荒地面积占比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了2019年的2%。

林中象道
物种分布模型结果表示,南滚河象群倾向栖息于远离人类聚居区的低海拔混交林,经模型预测,2019年研究区域内共有34km²的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和25km²的边缘适宜生境,其中大部分适宜栖息地分布在象群目前生活的保护区西部核心区,还有9km²的适宜栖息地被预测分布在保护区中部亚洲象历史分布区内,但此区域内目前并无亚洲象种群分布。

在过去30年内,南滚河象群失去了约三分之二的栖息地,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地土地利用的变化:1989年后,橡胶林和农田用地呈现持续扩张的趋势,保护区西部两个村庄的规模也扩张了3倍以上;增加了南滚河象群的孤立程度。

(a)1989年(b)2004年和(c)2019年南滚河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分布,以及(d)1989-2019年,(e)2004-2019年,和(f)1989-2004年间适宜栖息地分布变化。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南滚河亚洲象群的活动范围就在不断缩小。截至2004年,位于保护区中部的实验区已找不到南滚河象群的踪迹,随后中缅边境的两处迁徙廊道也不再为象群所用。

1989年、2004年和2019年南滚河保护区土地利用和亚洲象分布模式。浅色圈内为不同年份南滚河象群的分布范围。
通过分析发现南滚河象群近期并没有出现种群瓶颈的迹象,这证明目前的小种群来源于历史上较大的中-缅种群,由于中缅边境的土地利用变化而导致了种群规模的收缩,目前保护区西部核心区已经成为了南滚河亚洲象最后的庇护所。

目前保护区内亚洲象适宜栖息地面积仅为34km²,结合亚洲象的家域范围和环境承载力分析,这片栖息地只能容纳约18头亚洲象生存,而经本研究调查,南滚河象群的最小种群数量为22头,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南滚河象群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仅存适宜栖息地的承载力。若保护区内无法提供更多的适宜栖息地面积,南滚河象群的种群数量就很难进一步发展。
即便如此,我们的研究证明南滚河保护区在缓解土地利用变化和促进天然林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保护区外耕地和橡胶种植园的面积呈增加趋势的情况下,上述用地面积在保护区内则有所减少。得益于国家积极推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等保护项目和政策,保护区内也有32km²的森林恢复。

南滚河保护区拍摄亚洲象影像
中期看来,若恢复保护区中部实验区的适宜栖息地,并打通其与西部适宜栖息地的连通,将可以为额外14头亚洲象提供生息场所,这需要将区域内两个村庄的约800户居民重新安置,并废弃附近的农业和种植业用地,同时将这部分实验区划为保护区核心区,严格禁止任何人类活动。结合保护区内适宜栖息地范围的增加,从附近的勐养-普洱地区或尚勇-勐腊地区转入外部亚洲象个体,可以为南滚河象群提供新的生机。

南滚河保护区拍摄亚洲象影像
长期来看,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土地所有权将中缅边境的生态廊道从目前的橡胶林恢复为天然林,结合中-缅跨境合作,恢复栖息地连通性,解决南滚河象群目前的孤立状态,助力南滚河象群的对外种群交流,缓解近交衰退,保障象群的基因多样性,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南滚河象群的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亚洲象等濒危物种跨境区域种群及栖息地调查”项目和陆桥生态中心“2016年南滚河亚洲象拯救保护”项目资助。同时感谢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以及所有参加野外调查工作的学生和管护员对项目工作的大力支持。

Citation: Chen Y, Sun Y, Atzeni L et al. (2021). Anthropogenic pressures increase extinction risk of an isolated Asian elephant (Elephas maximus) population in southwestern China, as revealed by a combination of molecular- and landscape-scale approaches. Integrative Zoology 00, 1–17.


详情请见文章原文,欢迎交流、指正!
通讯作者:北京林业大学,时坤
邮箱:kunshi@bjfu.edu.cn
本文来自陆桥,欢迎转发;如需转载请联系
xiaoyin.wang@eco-bridgecontinental.org







